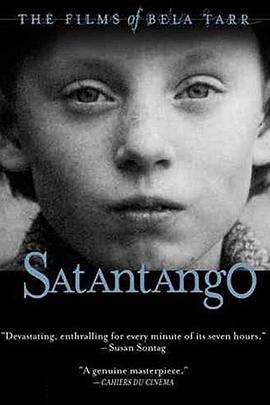看这部七小时十九分钟的巨制之前,我做好了枯燥的准备,没成想开头竟有些希区柯克式的诱人。
但这种悬疑感很快就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淹没。壮汉伊里米亚斯自己像「风雨中的小树枝」时,我突然想问:如果他这种能把村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操控者都只是树枝,那我这种文弱书生算什么?大概只是随风乱飘的小树叶吧。
这其实就是电影的基调:在这场不停歇的大雨里,没有人是获胜,我们都在跳一支原地打转的探戈。伊里米亚斯看似掌控全局,但如海明威小说标题:胜者一无所获。
伊里米亚斯有种矛盾的魅力,如果不做骗子,没准是个匈牙利低配版切·格瓦拉。在废墟中那句「你没有看到,我们正在为无望的人类尊严打游击战吗?」直接把诈骗和告密升华成了存在主义抵抗。
但我更忘不了他对跟班佩奇纳的嘲讽:「你总说我们的时候到了,我们的时候到了,但这辈子我们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到。」
那一瞬间,我脑子里自动播放起了新裤子乐队的《我们的时代》。这两个穿着长风衣走在破败街道上的匈牙利流浪汉,和彭磊声嘶力竭地「啦啦啦啦」融合在了一起。
更有意思的是其中的权力结构。佩奇纳虽然唯唯诺诺,但吃饭时也是自顾自大快朵颐。完全不管大哥伊里米亚斯。
而伊里米亚斯在村民面前是神,一见到地位更高的普莱尔(甘德勒),即刻臣服。这反倒更像是一种中国式的权力结构。
可为什么大家都要臣服?
那个坐在巨大桌子后面的上尉说:「自由与人类无关……人们害怕自由,但自由没什么可怕的,相反,秩序经常吓人。」
正是因为自由其实不可怕,那种绝对服从的秩序才需要通过「吓人」的方式来维持。
这种秩序的具体执行者,就是第十一章节里那两个平庸的办事员。一个根据伊里米亚斯充满文学性的告密信口述村民们的日常,并将其转译为他认为的大白话,一个用「二指禅」笨拙地戳着键盘,休息时切着午餐肉罐头吃。
就是这两个看起来滑稽、吃相难看的人,决定了所有村民的命运。毁灭你的不是恶魔,而是体制内一张沾着猪肝酱味儿的打字纸。
所以,当酒吧老板喊着「这里总有一天会有秩序!」时,那不是希望,那是绝望。在当权者看来,这里一直都很有秩序——一种压抑人性的、死寂的秩序。
在这种秩序下,最先破碎的一定是最脆弱的东西。
最让我致郁的是那个叫 Estike 的小女孩。她抱着死猫穿过荒野的样子,是我看电影这么多年最难熬的一段。
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里的玛蒂尔达,只可惜她没遇到杀手莱昂。她手里只有一只被她毒死的猫,和一个对她彻底关闭的世界。她虐猫是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掌控的东西,她自杀则让我想起太宰治总是与人相约自杀的事,某些时刻死亡是唯一的出口。
这种绝望甚至渗透到了人以外的东西。第八章结尾那只演技出众的猫头鹰,偶尔眨一只眼,盯着人类;到了第十章,那辆只有一个雨刷在动的破车,像极了那只猫头鷹。
这个世界是残缺的、半盲的,无论那个雨刷怎么摆动,都刷不净挡风玻璃上的污泥浊水。
最后,是那个贯穿全片的医生,一个正在做监控笔记的侦探。
记得周孝正讲座里说过,七情六欲需要物质基础,基础不够,欲望就会减少。
他说原始人就两欲:食色性也。而在这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村子里,很多人连性欲都没了,就像那个疑似妓女的女人说的:「人对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。」
电影最后,医生走向小礼拜堂,遇见那个发疯的敲钟人。疯子嘴里喊着「土耳其人来了!」,但在我耳朵里,那机械重复的节奏,怎么听怎么像是在喊「一二一!一二一!」。
那一刻,沉重的历史创伤(土耳其入侵)变成了一场荒诞的中学生跑步。没有神迹,没有救赎,只有一个疯子在废墟里指挥着一支看不见的幽灵军队,做着标准的队列训练。
这大概就是全部的真相了。
说实话,这个村子给我的感觉,正是我的初中时代。那种封闭、压抑、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去的感觉,甚至比电影里还绝望。
医生最后把那句「十月底的一个清晨」写在了本子上,故事回到了原点。撒旦的探戈跳完了一圈,又回到了开始。
窗户被钉上了木板,最后的光明重归于黑暗。
郝海龙
2025年12月14日在路上草就